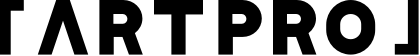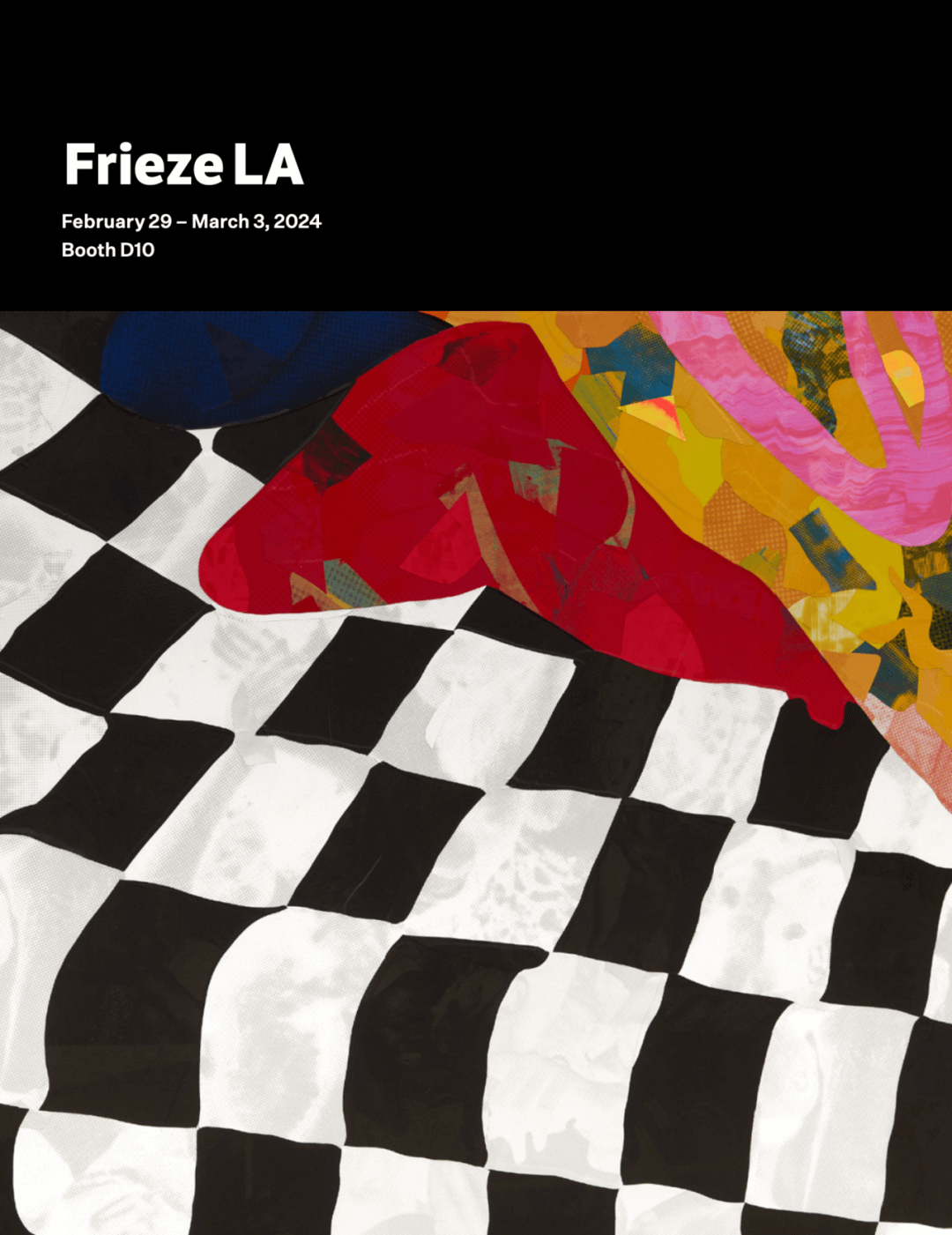博覽會|佩斯畫廊參加 2024 洛杉磯弗里茲藝博會 展位 D10

洛杉磯弗里茲藝博會
2024 Frieze Los Angeles
2024年2月29日至3月3日
聖莫妮卡機場
佩斯畫廊
展位 D10
佩斯畫廊將於2024年2月29日至3月3日參加2024年洛杉磯弗里茲藝博會(Frieze Los Angeles),於展位D10呈現許多全球及加州本地藝術家的代表性作品。
這次佩斯的展位中心由五位藝術家的作品共同組成,他們分別將於今年在佩斯洛杉磯空間舉辦個展,包括阿麗佳·柯維德(Alicja Kwade)最近創作的混合媒材雕塑作品《Know-ledge (Immortality-Maximilian)》(2023),她將與佩斯畫廊創始人兼總裁阿尼·格里姆徹合作,於5月親自策劃她和艾格尼絲·馬丁(Agnes Martin)的雙人展;戈登·帕克斯(Gordon Parks)於1966年創作的一件攝影作品,她的作品將於今夏展出;托克瓦斯·戴森(Torkwase Dyson)的全新繪畫,除了即將在洛杉磯佩斯舉辦的個展外,她的作品還將作為保羅·蓋蒂博物館“PST ART:藝術碰撞科學”展覽中畫廊項目的一部分展出;以及洛伊·霍洛威爾(Loie Hollowell)近期創作的一件「分割球體」(Split Orb)系列繪畫,除了即將在佩斯紐約和洛杉磯空間舉辦的個展之外,她還將在位於康涅狄格州里奇菲爾德的奧爾德里奇當代美術館(Aldrich Contemporary Art Museum)舉辦她的首次博物館回顧展。
自2022年佩斯在洛杉磯設立其美國西海岸的旗艦空間以來,畫廊持續深入這座城市的藝術社群。早在1960年代,佩斯就與洛杉磯的重要藝術家(包括加州光與太空運動的主要人物)建立密切聯繫。羅伯特歐文(Robert Irwin)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作為一位極具影響力且不斷銳意實驗的藝術家,光與空間是其繪畫、雕塑及裝置作品中的關鍵媒介。歐文的壁掛雕塑《#3 x 6' D Four Fold》(2016)將在本次佩斯的展位上亮相,這也是自去年歐文以95歲高齡離世後,畫廊首次公開展出其作品。
佩斯亦將呈現生活並工作於洛杉磯的藝術家——格倫·凱諾(Glenn Kaino)與梅莎·莫哈梅迪(Maysha Mohamedi)的新作,進一步融入這座城市現今充滿活力的當代藝術場景。其中凱諾的青銅及織物雕塑《Kabuto (LA) 》(2023)將在現場展位上亮相,他在佩斯紐約旗艦空間的首次大型個展“與虎同行”(Walking with a Tiger)於2月24日剛剛結束;他的作品最近還在洛杉磯日裔美國人國家博物館(Japanese American National Museum)的展覽“格倫·凱諾:阿基的集市“(Glenn Kaino: Aki's Market)中展出,這是一個關注其祖父的東洛杉磯生活的多面裝置。佩斯也將展出莫哈梅迪2024年最新完成的繪畫作品,作為一位自學成才的藝術家,她成長於聖路易斯奧比斯波,以氣韻獨特的抽象畫廣為人知。
在紙上作品方面,佩斯將帶來羅戈(Robert Longo)一幅描繪棕櫚樹這一南加州美景的永恆象徵的巨幅炭筆畫,並與巴勃羅·畢卡索(Pablo Picasso)的《Le peintre et son modèle》(1970)一同展出。去年,佩斯曾在紐約旗艦空間為畢卡索舉辦了聚焦其草稿與速寫作品的大型展覽「畢卡索:14個速寫本」。在這些草圖的基礎上,畢卡索構思了其日後許多著名的繪畫和雕塑作品。就在1973年——在他去世的前三年,畢卡索用鋼筆、墨水和水彩創作了這件《Le peintre et son modèle》。
琳達·本格里斯(Lynda Benglis)、多諾萬(Tara Donovan)和路易斯·內維爾森(Louise Nevelson)等數位跨越世代的女性藝術家的雕塑作品也將在佩斯畫廊展位上佔據重要位置。本格里斯創作於2023年的全新壁掛雕塑將與她1968年的作品《Shape Shifter》一同展出,這是她早期使用澆注顏料乳膠進行的實驗之一。此外,內維爾森於1985年創作的黑漆木雕,以及多諾萬最新創作的由CD組成的創新作品也將亮相展位現場。
亮點作品
Highlights
1979年生於波蘭卡托維茲
現工作、生活於德國
《Know-ledge (Immortality-Maximilian)》(2023)探討了知識、歷史和將大量資訊提煉為其基本本質的嘗試之間的動態關係。三卷《布列塔尼卡百科全書》按字母順序記錄了從“不朽”到“馬克西米利安”的條目,支撐著一塊看似生長的岩石,從大理石基座的兩側溢出。穿透這個系統的是一個蟲洞;根據生於德國的理論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的一個場方程的解法,蟲洞是時空中的一個假想的隧道狀結構,可以連接宇宙中的不同點。柯維德將蟲洞想像成球形的喇叭狀開口,由一條狹窄的通道相連,隱喻在岩石(代表古老的地球)和書籍(象徵人類知識和時間的整合)之間構建了一個通道。 1771年,《布列塔尼卡百科全書》首次出版,當時的構想是將其作為一個框架來整理和「傳播科學知識」(diffuse the Knowledge of Science)。在柯維德的整個作品中,藝術家都在追問訊息的起源,她的作品就像是一部思想百科全書,或者說是「認識事物的雕塑嘗試」(sculptural attempts at understanding)。
古代石材與現代材料的並置是柯維德材料探索的特徵,它綜合了從啟蒙時代《大英百科全書》的願望到蟲洞形式的推測性科學探索等獨特元素,彌合了人類認識發展過程中固有的時間和概念差距。
1966年5月21日,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擊敗挑戰者亨利·庫柏(Henry Cooper),成功衛冕重量級拳王頭銜。同年,阿里認識了攝影師戈登·帕克斯(Gordon Parks),後者當時正在為《生活》雜誌準備有關這位偶像級拳擊手的稿件內容;《Untitled, London, England》(1966/2020)便是這次成果豐厚的合作中所產生的眾多攝影作品之一。
在這件作品中,阿里雖身處拳擊場外,但仍心繫拳擊:他站在陰影內,右臂收至胸前,手握成拳,做出保護性防衛姿勢。他的臉部被緊緊勒起的兜帽覆蓋,極富戲劇性的光線投射在他的眼睛和下巴上,突顯出他的鼻子與顴骨。拳王顯得措手不及,甚至有些脆弱。帕克斯的攝影實踐致力於記錄美國的生活與文化,關注社會正義和非裔美國人的遭遇,他在阿里身上找到了完美的主題。 《Untitled, London, England》從心理層面揭示了這位英雄拳擊手的內心世界,在當時也備受爭議。兩年前,阿里因皈依伊斯蘭教並將自己的名字從卡修斯·克萊(Cassius Clay)改為穆罕默德·阿里而成為全國頭條新聞。他因反白人情緒和反對越戰而受到抨擊。在這篇《生活》雜誌的人物專題中,帕克斯將鏡頭對準聚拳擊手的私密場景──阿里躺在更衣室的桌子上,或是被一位年輕粉絲熱情擁抱──讓讀者對拳擊手的內心世界更感同身受。
1941年生於路易斯安那州查爾斯湖
琳達·本格里斯的《Treble Bar (Minor) 》(2023)屬於藝術家最近創作的阿巴卡紙雕塑系列。本格里斯使用原產於菲律賓香蕉樹-阿巴卡的紙漿製作手工紙張,然後將其包覆在竹葦中。這些作品被放置在她位於新墨西哥州的工作室外的陽光下晾乾,這種暴露在自然環境中的狀態有助於決定作品的最終形態;在晾曬期間,紙張會緊緊裹住竹葦收縮,就像包覆肋骨上的皮膚一樣。評論家羅伯特平卡斯-威滕(Robert Pincus-Witten)在1973年出版的《藝術論壇》(Artforum)上指出,「凝固的姿態」(藝術家語)是她創作實踐的核心,標誌著她的作品體現了對立的特質──既有生理上的,也有心理上的。藝術家在製作每件雕塑作品後,都會為其賦予一個標題,這件作品的標題參考了一種名為“Treble-bar”的飛蛾,這種飛蛾生活於不列顛群島和北極地區,以其三角形的翅膀和每片前翅上三條獨特的黑色條帶為特徵,並因此而得名。 《Treble Bar (Minor)》延續了本格里斯對手工製品和自然力量塑造的物品之間二元對立的探索,進一步發展了她早期用紙和鐵絲網製作的作品,將自然物和無機物並置,延續了其作品的核心。
塔拉·多諾萬以其基於過程和系統的雕塑、裝置、繪畫和版畫作品而聞名,她經常研究日常材料和物品的護身符屬性,無論是紐扣、泡沫塑料杯、鉛筆、圖釘還是電子屏幕和彈簧玩具均為她所用。透過累積、聚合和迭代,她將材料轉化為變形的藝術品,探索人類感知的可能性和限制。在她的最新作品中,藝術家將重點放在了發現的、撿拾的和升級再造的光碟的視覺特性上。根據一天中的不同時間和觀眾的不同視角,這些圖騰柱狀的雕塑的折射表面會呈現不同的光學效果。多諾萬的新作可變性極強,以栩栩如生的形式直接回應了觀眾穿越空間時身體的存在,反映出她對感知細微差別和材料變形之間關係的濃厚興趣。同時,這些作品也邀請觀眾思考如何將一種曾經用於儲存和傳輸數位訊息的過時媒介轉變為一種身體體驗的棱鏡。
肯尼斯·諾蘭的《Untitled》(1981)同時體現出藝術家在1960年代繪畫中的標誌性條紋以及他向異形畫布的實驗性轉變。其優雅的冷色調散發出靜謐之感,而畫布上棱角分明的邊框則提供了速度、動態和方向的複調結構。在諾蘭的整個藝術生涯中,他對色彩表現潛力的興趣從未消退,不斷推動色彩的形式表達以應對新的問題。 1940年代,諾蘭在黑山學院師從色彩理論家約瑟夫·阿爾伯斯(Josef Albers),並在此基礎上創立了華盛頓色彩畫派,其成員包括共同創始人路易斯·莫里斯(Louis Morris )、山姆·吉利安(Sam Gilliam)和阿爾瑪·托馬斯(Alma Thomas)等人。他們的作品對美國戰後抽象派視覺語言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最終為極簡主義奠定了基礎。諾蘭絕妙而飽和的色彩受到其同門前輩、畫家海倫·弗蘭肯特爾(Helen Frankenthaler)的啟發,透過將丙烯顏料浸泡在未上底漆的原始畫布上而實現。到70年代中期,他早期畫面中的」簡單「秩序讓位給新的複雜性。轉向畫布結構本身,諾蘭開始建構不對稱的、有稜角的畫框,既堅持繪畫的物質性,又作為空間和維度的幻覺表現。
諾蘭在1977年與當年古根漢回顧展的策展人黛安娜·沃爾德曼(Diane Waldman)的一次談話中解釋說:「我一直在想,如果某件東西不平衡,它會是什麼樣子?…在嘗試了包括矩形、菱形在內的對稱圖形,以及各種形狀的極端變形之後,我才最終意識到:一切都是不平衡的,這世上沒有垂直的,沒有水平的,也沒有平行的東西。」《Untitled》將他現代主義時期的條紋語言與後現代畫布結構的重新配置結合在一起,成為托馬斯·麥克艾維裡(Thomas McEvilly)所說的」自我指涉的形式主義演變」(self-referential formalist evolution)。
更多信息,請點擊卡片
更多全球藝術市場的最新動態請持續關注 ArtPro。